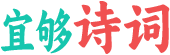世说新语·文学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| 《世说新语》 刘义庆 著 《世说新语》是中国南朝宋时期(420-581年)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。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(403-444年)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,梁代刘峻作注。全书原八卷,刘峻注本分为十卷,今传本皆作三卷,分为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、方正、雅量等三十六门,全书共一千多则,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,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、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。 |
世说新语·文学
郑玄在马融门下,三年不得相见,高足弟子传授而已。尝算浑天不合,诸弟子莫能解。或言玄能者,融召令算,一转便决,众咸骇服。及玄业成辞归,既而融有“礼乐皆东”之叹。恐玄擅名而心忌焉。玄亦疑有追,乃坐桥下,在水上据屐。融果转式逐之,告左右曰:“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,此必死矣。”遂罢追,玄竟以得免。
郑玄欲注春秋传,尚未成时,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,先未相识,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。玄听之良久,多与己同。玄就车与语曰:“吾久欲注,尚未了。听君向言,多与吾同。今当尽以所注与君。”遂为服氏注。
郑玄家奴婢皆读书。尝使一婢,不称旨,将挞之。方自陈说,玄怒,使人曳箸泥中。须臾,复有一婢来,问曰:“胡为乎泥中?”答曰:“薄言往愬,逢彼之怒。”
服虔既善春秋,将为注,欲参考同异;闻崔烈集门生讲传,遂匿姓名,为烈门人赁作食。每当至讲时,辄窃听户壁间。既知不能踰己,稍共诸生叙其短长。烈闻,不测何人,然素闻虔名,意疑之。明蚤往,及未寤,便呼:“子慎!子慎!”虔不觉惊应,遂相与友善。
钟会撰四本论,始毕,甚欲使嵇公一见。置怀中,既定,畏其难,怀不敢出,于户外遥掷,便回急走。
何晏为吏部尚书,有位望,时谈客盈坐,王弼未弱冠往见之。晏闻弼名,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:“此理仆以为极,可得复难不?”弼便作难,一坐人便以为屈,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,皆一坐所不及。
何平叔注老子,始成,诣王辅嗣。见王注精奇,迺神伏曰:“若斯人,可与论天人之际矣!”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。
王辅嗣弱冠诣裴徽,徽问曰:“夫无者,诚万物之所资,圣人莫肯致言,而老子申之无已,何邪?”弼曰:“圣人体无,无又不可以训,故言必及有;老、庄未免于有,恒训其所不足。”
傅嘏善言虚胜,荀粲谈尚玄远。每至共语,有争而不相喻。裴冀州释二家之义,通彼我之怀,常使两情皆得,彼此俱畅。
何晏注老子未毕,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。何意多所短,不复得作声,但应诺诺。遂不复注,因作道德论。
中朝时,有怀道之流,有诣王夷甫咨疑者。值王昨已语多,小极,不复相酬答,乃谓客曰:“身今少恶,裴逸民亦近在此,君可往问。”
裴成公作崇有论,时人攻难之,莫能折。唯王夷甫来,如小屈。时人即以王理难裴,理还复申。
诸葛宏年少不肯学问。始与王夷甫谈,便已超诣。王叹曰:“卿天才卓出,若复小加研寻,一无所愧。”宏后看庄、老,更与王语,便足相抗衡。
卫玠总角时问乐令“梦”,乐云“是想”。卫曰:“形神所不接而梦,岂是想邪?”乐云:“因也。未尝梦乘车入鼠穴,捣齑啖铁杵,皆无想无因故也。”卫思“因”,经日不得,遂成病。乐闻,故命驾为剖析之。卫既小差。乐叹曰:“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!”
庾子嵩读庄子,开卷一尺许便放去,曰:“了不异人意。”
客问乐令“旨不至”者,乐亦不复剖析文句,直以麈尾柄确几曰:“至不?”客曰:“至!”乐因又举麈尾曰:“若至者,那得去?”于是客乃悟服。乐辞约而旨达,皆此类。
初,注庄子者数十家,莫能究其旨要。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,妙析奇致,大畅玄风。唯秋水、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。秀子幼,义遂零落,然犹有别本。郭象者,为人薄行,有俊才。见秀义不传于世,遂窃以为己注。乃自注秋水、至乐二篇,又易马蹄一篇,其余众篇,或定点文句而已。后秀义别本出,故今有向、郭二庄,其义一也。
阮宣子有令闻,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:“老、庄与圣教同异?”对曰:“将无同?”太尉善其言,辟之为掾。世谓“三语掾”。卫玠嘲之曰:“一言可辟,何假于三?”宣子曰:“苟是天下人望,亦可无言而辟,复何假一?”遂相与为友。
裴散骑娶王太尉女。婚后三日,诸婿大会,当时名士,王、裴子弟悉集。郭子玄在坐,挑与裴谈。子玄才甚丰赡,始数交未快。郭陈张甚盛,裴徐理前语,理致甚微,四坐咨嗟称快。王亦以为奇,谓诸人曰:“君辈勿为尔,将受困寡人女婿!”
卫玠始度江,见王大将军。因夜坐,大将军命谢幼舆。玠见谢,甚说之,都不复顾王,遂达旦微言。王永夕不得豫。玠体素羸,恒为母所禁。尔夕忽极,于此病笃,遂不起。
旧云:王丞相过江左,止道声无哀乐、养生、言尽意,三理而已。然宛转关生,无所不入。
殷中军为庾公长史,下都,王丞相为之集,桓公、王长史、王蓝田、谢镇西并在。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,语殷曰:“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。”既共清言,遂达三更。丞相与殷共相往反,其余诸贤,略无所关。既彼我相尽,丞相乃叹曰:“向来语,乃竟未知理源所归,至于辞喻不相负。正始之音,正当尔耳!”明旦,桓宣武语人曰:“昨夜听殷、王清言甚佳,仁祖亦不寂寞,我亦时复造心,顾看两王掾,辄翣如生母狗馨。”
殷中军见佛经云:“理亦应阿堵上。”
谢安年少时,请阮光禄道白马论。为论以示谢,于时谢不即解阮语,重相咨尽。阮乃叹曰:“非但能言人不可得,正索解人亦不可得!”
褚季野语孙安国云:“北人学问,渊综广博。”孙答曰:“南人学问,清通简要。”支道林闻之曰:“圣贤固所忘言。自中人以还,北人看书,如显处视月;南人学问,如牖中窥日。”
刘真长与殷渊源谈,刘理如小屈,殷曰:“恶,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。”
殷中军云:“康伯未得我牙后慧。”
谢镇西少时,闻殷浩能清言,故往造之。殷未过有所通,为谢标榜诸义,作数百语。既有佳致,兼辞条丰蔚,甚足以动心骇听。谢注神倾意,不觉流汗交面。殷徐语左右:“取手巾与谢郎拭面。”
宣武集诸名胜讲易,日说一卦。简文欲听,闻此便还。曰:“义自当有难易,其以一卦为限邪?”
有北来道人好才理,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,讲小品。于时竺法深、孙兴公悉共听。此道人语,屡设疑难,林公辩答清析,辞气俱爽。此道人每辄摧屈。孙问深公:“上人当是逆风家,向来何以都不言?”深公笑而不答。林公曰:“白旃檀非不馥,焉能逆风?”深公得此义,夷然不屑。
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,往反精苦,客主无闲。左右进食,冷而复暖者数四。彼我奋掷麈尾,悉脱落,满餐饭中。宾主遂至莫忘食。殷乃语孙曰:“卿莫作强口马,我当穿卿鼻。”孙曰:“卿不见决鼻牛,人当穿卿颊。”
庄子逍遥篇,旧是难处,诸名贤所可钻味,也而不能拔理于郭、向之外。支道林在白马寺中,将冯太常共语,因及逍遥。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,立异义于众贤之外,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。后遂用支理。
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。良久,殷理小屈,游辞不已,刘亦不复答。殷去后,乃云:“田舍儿,强学人作尔馨语。”
殷中军虽思虑通长,然于才性偏精。忽言及四本,便苦汤池铁城,无可攻之势。
支道林造即色论,论成,示王中郎。中郎都无言。支曰:“默而识之乎?”王曰:“既无文殊,谁能见赏?”
王逸少作会稽,初至,支道林在焉。孙兴公谓王曰:“支道林拔新领异,胸怀所及,乃自佳,卿欲见不?”王本自有一往隽气,殊自轻之。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,王都领域,不与交言。须臾支退,后正值王当行,车已在门。支语王曰:“君未可去,贫道与君小语。”因论庄子逍遥游。支作数千言,才藻新奇,花烂映发。王遂披襟解带,留连不能已。
三乘佛家滞义,支道林分判,使三乘炳然。诸人在下坐听,皆云可通。支下坐,自共说,正当得两,入三便乱。今义弟子虽传,犹不尽得。
许掾年少时,人以比王苟子,许大不平。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,王亦在焉。许意甚忿,便往西寺与王论理,共决优劣。苦相折挫,王遂大屈。许复执王理,王执许理,更相覆疏;王复屈。许谓支法师曰:“弟子向语何似?”支从容曰:“君语佳则佳矣,何至相苦邪?岂是求理中之谈哉!”
林道人诣谢公,东阳时始总角,新病起,体未堪劳。与林公讲论,遂至相苦。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,再遣信令还,而太傅留之。王夫人因自出云:“新妇少遭家难,一生所寄,唯在此儿。”因流涕抱儿以归。谢公语同坐曰:“家嫂辞情慷慨,致可传述,恨不使朝士见。”
支道林、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。支为法师,许为都讲。支通一义,四坐莫不厌心。许送一难,众人莫不抃舞。但共嗟咏二家之美,不辩其理之所在。
谢车骑在安西艰中,林道人往就语,将夕乃退。有人道上见者,问云:“公何处来?”答云:“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。”
支道林初从东出,住东安寺中。王长史宿构精理,并撰其才藻,往与支语,不大当对。王叙致作数百语,自谓是名理奇藻。支徐徐谓曰:“身与君别多年,君义言了不长进。”王大惭而退。
殷中军读小品,下二百签,皆是精微,世之幽滞。尝欲与支道林辩之,竟不得。今小品犹存。
佛经以为袪练神明,则圣人可致。简文云:“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?然陶练之功,尚不可诬。”
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,后精渐归支,意甚不忿,遂遁迹剡下。遣弟子出都,语使过会稽。于时支公正讲小品。开戒弟子:“道林讲,比汝至,当在某品中。”因示语攻难数十番,云:“旧此中不可复通。”弟子如言诣支公。正值讲,因谨述开意。往反多时,林公遂屈。厉声曰:“君何足复受人寄载!”
殷中军问:“自然无心于禀受。何以正善人少,恶人多?”诸人莫有言者。刘尹答曰:“譬如写水著地,正自纵横流漫,略无正方圆者。”一时绝叹,以为名通。
康僧渊初过江,未有知者,恒周旋市肆,乞索以自营。忽往殷渊源许,值盛有宾客,殷使坐,粗与寒温,遂及义理。语言辞旨,曾无愧色。领略粗举,一往参诣。由是知之。
殷、谢诸人共集。谢因问殷:“眼往属万形,万形来入眼不?”
人有问殷中军:“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,将得财而梦矢秽?”殷曰:“官本是臭腐,所以将得而梦棺尸;财本是粪土,所以将得而梦秽污。”时人以为名通。
殷中军被废东阳,始看佛经。初视维摩诘,疑般若波罗密太多,后见小品,恨此语少。
支道林、殷渊源俱在相王许。相王谓二人:“可试一交言。而才性殆是渊源崤、函之固,君其慎焉!”支初作,改辙远之,数四交,不觉入其玄中。相王抚肩笑曰:“此自是其胜场,安可争锋!”
谢公因子弟集聚,问毛诗何句最佳?遏称曰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公曰:“訏谟定命,远猷辰告。”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。
张凭举孝廉出都,负其才气,谓必参时彦。欲诣刘尹,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。张遂诣刘。刘洗濯料事,处之下坐,唯通寒暑,神意不接。张欲自发无端。顷之,长史诸贤来清言。客主有不通处,张乃遥于末坐判之,言约旨远,足畅彼我之怀,一坐皆惊。真长延之上坐,清言弥日,因留宿至晓。张退,刘曰:“卿且去,正当取卿共诣抚军。”张还船,同侣问何处宿?张笑而不答。须臾,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,同侣惋愕。即同载诣抚军。至门,刘前进谓抚军曰:“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!”既前,抚军与之话言,咨嗟称善曰:“张凭勃窣为理窟。”即用为太常博士。
汰法师云:“‘六通’、‘三明’同归,正异名耳。”
支道林、许、谢盛德,共集王家。谢顾谓诸人:“今日可谓彦会,时既不可留,此集固亦难常。当共言咏,以写其怀。”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?正得渔父一篇。谢看题,便各使四坐通。支道林先通,作七百许语,叙致精丽,才藻奇拔,众咸称善。于是四坐各言怀毕。谢问曰:“卿等尽不?”皆曰:“今日之言,少不自竭。”谢后粗难,因自叙其意,作万余语,才峰秀逸。既自难干,加意气拟托,萧然自得,四坐莫不厌心。支谓谢曰:“君一往奔诣,故复自佳耳。”
殷中军、孙安国、王、谢能言诸贤,悉在会稽王许。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。孙语道合,意气干云。一坐咸不安孙理,而辞不能屈。会稽王慨然叹曰:“使真长来,故应有以制彼。”既迎真长,孙意己不如。真长既至,先令孙自叙本理。孙粗说己语,亦觉殊不及向。刘便作二百许语,辞难简切,孙理遂屈。一坐同时拊掌而笑,称美良久。
僧意在瓦官寺中,王苟子来,与共语,便使其唱理。意谓王曰:“圣人有情不?”王曰:“无。”重问曰:“圣人如柱邪?”王曰:“如筹算,虽无情,运之者有情。”僧意云:“谁运圣人邪?”苟子不得答而去。
司马太傅问谢车骑:“惠子其书五车,何以无一言入玄?”谢曰:“故当是其妙处不传。”
殷中军被废,徙东阳,大读佛经,皆精解。唯至“事数”处不解。遇见一道人,问所签,便释然。
殷仲堪精核玄论,人谓莫不研究。殷乃叹曰:“使我解四本,谈不翅尔。”
殷荆州曾问远公:“易以何为体?”答曰:“易以感为体。”殷曰:“铜山西崩,灵钟东应,便是易耶?”远公笑而不答。
羊孚弟娶王永言女。及王家见婿,孚送弟俱往。时永言父东阳尚在,殷仲堪是东阳女婿,亦在坐。孚雅善理义,乃与仲堪道齐物。殷难之,羊云:“君四番后,当得见同。”殷笑曰:“乃可得尽,何必相同?”乃至四番后一通。殷咨嗟曰:“仆便无以相异。”叹为新拔者久之。
殷仲堪云:“三日不读道德经,便觉舌本闲强。”
提婆初至,为东亭第讲阿毗昙。始发讲,坐裁半,僧弥便云:“都已晓。”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更就余屋自讲。提婆讲竟,东亭问法冈道人曰:“弟子都未解,阿弥那得已解?所得云何?”曰:“大略全是,故当小未精核耳。”
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,每相攻难。年余后,但一两番。桓自叹才思转退。殷云:“此乃是君转解。”
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,不成者行大法。应声便为诗曰:“煮豆持作羹,漉菽以为汁。萁在釜下然,豆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?”帝深有惭色。
魏朝封晋文王为公,备礼九锡,文王固让不受。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。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。籍时在袁孝尼家,宿醉扶起,书札为之,无所点定,乃写付使。时人以为神笔。
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,时人互有讥訾,思意不惬。后示张公。张曰:“此二京可三,然君文未重于世,宜以经高名之士。”思乃询求于皇甫谧。谧见之嗟叹,遂为作叙。于是先相非贰者,莫不敛衽赞述焉。
刘伶著酒德颂,意气所寄。
乐令善于清言,而不长于手笔。将让河南尹,请潘岳为表。潘云:“可作耳。要当得君意。”乐为述己所以为让,标位二百许语。潘直取错综,便成名笔。时人咸云:“若乐不假潘之文,潘不取乐之旨,则无以成斯矣。”
夏侯湛作周诗成,示潘安仁。安仁曰:“此非徒温雅,乃别见孝悌之性。”潘因此遂作家风诗。
孙子荆除妇服,作诗以示王武子。王曰:“未知文生于情,情生于文。览之凄然,增伉俪之重。”
太叔广甚辩给,而挚仲治长于翰墨,俱为列卿。每至公坐,广谈,仲治不能对。退著笔难广,广又不能答。
江左殷太常父子,并能言理,亦有辩讷之异。扬州口谈至剧,太常辄云:“汝更思吾论。”
庾子嵩作意赋成,从子文康见,问曰:“若有意邪?非赋之所尽;若无意邪?复何所赋?”答曰:“正在有意无意之间。”
郭景纯诗云:“林无静树,川无停流。”阮孚云:“泓峥萧瑟,实不可言。每读此文,辄觉神超形越。”
庾阐始作扬都赋,道温、庾云:“温挺义之标,庾作民之望。方响则金声,比德则玉亮。”庾公闻赋成,求看,兼赠贶之。阐更改“望”为“俊”,以“亮”为“润”云。
孙兴公作庾公诔。袁羊曰:“见此张缓。”于时以为名赏。
庾仲初作扬都赋成,以呈庾亮。亮以亲族之怀,大为其名价云:“可三二京,四三都。”于此人人竞写,都下纸为之贵。谢太傅云:“不得尔。此是屋下架屋耳,事事拟学,而不免俭狭。”
习凿齿史才不常,宣武甚器之,未三十,便用为荆州治中。凿齿谢笺亦云:“不遇明公,荆州老从事耳!”后至都见简文,返命,宣武问“见相王何如?”答云:“一生不曾见此人!”从此忤旨,出为衡阳郡,性理遂错。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,品评卓逸。
孙兴公云:“三都、二京,五经鼓吹。”
谢太傅问主簿陆退“张凭何以作母诔,而不作父诔?”退答曰:“故当是丈夫之德,表于事行;妇人之美,非诔不显。”
王敬仁年十三,作贤人论。长史送示真长,真长答云:“见敬仁所作论,便足参微言。”
孙兴公云:“潘文烂若披锦,无处不善;陆文若排沙简金,往往见宝。”
简文称许掾云:“玄度五言诗,可谓妙绝时人。”
孙兴公作天台赋成,以示范荣期,云:“卿试掷地,要作金石声。”范曰:“恐子之金石,非宫商中声!”然每至佳句,辄云:“应是我辈语。”
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,看竟,掷与坐上诸客曰:“此是安石碎金。”
袁虎少贫,尝为人佣载运租。谢镇西经船行,其夜清风朗月,闻江渚闲估客船上有咏诗声,甚有情致。所诵五言,又其所未尝闻,叹美不能已。即遣委曲讯问,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。因此相要,大相赏得。
孙兴公云:“潘文浅而净,陆文深而芜。”
裴郎作语林,始出,大为远近所传。时流年少,无不传写,各有一通。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,甚有才情。
谢万作八贤论,与孙兴公往反,小有利钝。谢后出以示顾君齐,顾曰:“我亦作,知卿当无所名。”
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,既成,公与时贤共看,咸嗟叹之。时王珣在坐云:“恨少一句,得‘写’字足韵,当佳。”袁即于坐揽笔益云:“感不绝于余心,泝流风而独写。”公谓王曰:“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。”
孙兴公道:“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,裁为负版裤,非无文采,酷无裁制。”
袁伯彦作名士传成,见谢公。公笑曰:“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,特作狡狯耳!彦伯遂以箸书。”
王东亭到桓公吏,既伏阁下,桓令人窃取其白事。东亭即于阁下更作,无复向一字。
桓宣武北征,袁虎时从,被责免官。会须露布文,唤袁倚马前令作。手不辍笔,俄得七纸,殊可观。东亭在侧,极叹其才。袁虎云:“当令齿舌闲得利。”
袁宏始作东征赋,都不道陶公。胡奴诱之狭室中,临以白刃,曰:“先公勋业如是!君作东征赋,云何相忽略?”宏窘蹙无计,便答:“我大道公,何以云无?”因诵曰:“精金百炼,在割能断。功则治人,职思靖乱。长沙之勋,为史所赞。”
或问顾长康:“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?”顾曰:“不赏者,作后出相遗。深识者,亦以高奇见贵。”
殷仲文天才宏瞻,而读书不甚广,博亮叹曰:“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,才不减班固。”
羊孚作雪赞云:“资清以化,乘气以霏。遇象能鲜,即洁成辉。”桓胤遂以书扇。
王孝伯在京行散,至其弟王睹户前,问:“古诗中何句为最?”睹思未答。孝伯咏“‘所遇无故物,焉得不速老?’此句为佳。”
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:“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。”因吟啸良久,随而下笔。一坐之闲,诔以之成。
桓玄初并西夏,领荆、江二州,二府一国。于时始雪,五处俱贺,五版并入。玄在听事上,版至即答。版后皆粲然成章,不相揉杂。
桓玄下都,羊孚时为兖州别驾,从京来诣门,笺云:“自顷世故睽离,心事沦蕰。明公启晨光于积晦,澄百流以一源。”桓见笺,驰唤前,云:“子道,子道,来何迟?”即用为记室参军。孟昶为刘牢之主簿,诣门谢,见云:“羊侯,羊侯,百口赖卿!”
世说新语文学译文
郑玄在马融门下求学,过了三年也没见着马融,只是由高才弟子为他讲授罢了。马融曾用浑天算法演算,结果不相符,弟子们也没有谁能理解。有人说郑玄能演算,马融便叫他来,要他演算,郑玄一算就解决了,大家都很惊奇,佩服。等到郑玄学业完成,辞别回家,马融随即慨叹礼和乐的中心都将要转移到东方去了,担心郑玄会独亨盛名,心里很忌恨他。郑玄也猜测马融会来追赶,便走到桥底下,在水里垫着木板鞋坐着。马融果然旋转式盘占卜郑玄踪迹,然后告诉身边的人说:“郑玄在土下、水上,靠着木头,这表明一定是死了。”便决定不去追赶。郑玄终于因此得免一死。
郑玄想要注释《左传》,还没有完成。这时有事到外地去,和服子慎相遇,住在同一个客店里,起初两人并不认识。服子慎在店外的车子上,和别人谈到自己注《左传》的想法;郑玄听了很久。听出服子愎的见解多数和自己相同。郑玄就走到车前对服子慎说道:“我早就想要注《左传》,还没有完成;听了您刚才的谈论,大多和我相同,现在应该把我作的注全部送给您。”终于成了服氏注。
郑玄家里的奴婢都读书。一次曾使唤一个婢女,事情干得不称心,郑玄要打她。她刚要分辩,郑玄生气了,叫人把她拉到泥里。一会儿.又有一个婢女走来,问她:“胡为乎泥中?”她回答说:“薄言往诉,逢彼之怒。”
服虔已经对《左传》很有研究,将要给它做注释,想参考各家的异同。他听说崔烈召集学生讲授《左传》,便隐姓埋名,去给崔烈的学生当佣人做饭。每当到讲授的时候,他就躲在门外偷听。等他了解到崔烈超不过自己以后,便渐渐地和那些学生谈论崔烈的得失。崔烈听说后,猜不出是什么人,可是一向听到过服虔的名声,猜想是他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拜访,趁服虔还没睡醒的时候,便突然叫:“子慎!子慎!”服虔不觉惊醒答应,从此两人就结为好友。
钟会撰著《四本论》刚刚完成,很想让嵇康看一看。便揣在怀里,揣好以后,又怕嵇康质疑问难,揣着不敢拿出,走到门外远远地扔进去,便转身急急忙忙地跑了。
何晏任吏部尚书时,很有地位声望,当时清谈的宾客常常满座,王弼年龄不到二十岁时,去拜会他。何晏听到过王弼的名声,便分条列出以前那些精妙的玄理来告诉王弼说:”这些道理我认为是谈得最透彻的了,还能再反驳吗?”王弼便提出反驳,满座的人都觉得何晏理屈。于是王弼反复自问自答,所谈玄理都晕存摩的人赶不上的。
何平叔注释《老子》才完成,就去拜会王辅嗣;看见王辅嗣的《老子注》见解精微独到,于是非常佩服。说:“像这个人,可以和他讨论天人关系的问题了!”于是把自己所注的改写成《道论》《德论》两篇。
王弼年轻时去拜访裴徽,裴徽问他:“无,确实是万物的根源,可是圣人不肯对它发表意见,老子却反复地陈述它,这是为什么?”王弼说:“圣人认为无是本体,可是无又不能解释清楚,所以言谈间必定涉及有;老子、庄子不能去掉有,所以要经常去解释那个还掌握得不充分的无。”
傅嘏擅长谈论虚胜,荀粲清谈崇尚玄远。每当两人到一起谈论的时候,发生争论,却又互不理解。冀州刺史裴徽能够解释清楚两家的道理,沟通彼此的心意,常使双方都感满意,彼此都能通晓。
何晏注释《老子》还没完成时,一次听王弼谈起自己注释《老子》的意旨,对比之下,何晏的见解很多地方有欠缺,何晏不敢再开口,只是连声答应“是是”。于是不再注释下去,便另写《道德论》。
西晋时,有一班倾慕道家学说的人,其中有人登门向王夷甫请教疑难,正碰上王夷甫前一天已经谈论了很久,有点疲乏,不想再和客人应对,便对客人说:“我现在有点不舒服,裴逸民也在我附近住,您可以去问他。”
裴逸民作《崇有论》,当时的人责难他,可是没有谁能驳倒他。只有王夷甫来和他辩论,他才有点理亏。当时的人就用王夷甫的理论来驳他,可是这时他的理论又显得头头是道了。
诸葛龙少年时不肯学习求教,可是一开始和王夷甫清谈,便已经显示出他的造诣很深。王夷甫感叹他说:“你的聪明才智很出众,如果再稍加研讨,就丝毫也不会比当代名流差了。”诸葛厷后来阅读了《庄子》《老子》,再和王夷甫清谈,便完全可以和他旗鼓相当了。
卫玠幼年时,问尚书令乐广为什么会做梦,乐广说是因为心有所想。卫玠说:“身体和精神都不曾接触过的却在梦里出现,这哪里是心有所想呢?”乐广说:“是沿袭做过的事。人们不曾梦见坐车进老鼠洞,或者捣碎姜蒜去喂铁杵,这都是因为没有这些想法,没有这些可模仿的先例。”卫玠便思索沿袭问题,成天思索也得不出答案,终于想得生了病。乐广听说后,特意坐车去给他分析这个问题。卫玠的病有了起色以后,乐广感慨他说:“这孩子心里一定不会得无法医治的病!”
庾子嵩读《庄子》,打开书读了一尺左右的篇幅就放下了,说道:“和我的想法完全相同。”
有位客人问尚书令乐广,“旨不至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乐广也不再分析这句话的词句,径直用拂尘柄敲着小桌子说:“达到了没有?”客人回答说:“达到了。”乐广于是又举起拂尘说:“如果达到了,怎么能离开呢?”这时客人才醒悟过来,表示信服。乐广解释问题时言辞简明扼要,可是意思很透彻,都是像上面这个例子一样
起初,注《庄子》的有几十家,可是没有一家能探索到它的要领。向秀推开旧注,另求新解,精到的分析,美妙的意趣,使《庄子》玄奥的意旨大为畅达。其中只有《秋水》《至乐》两篇的注还没有完成,向秀就死了。向秀的儿子还很小,不能完成父业,这两篇的注释便脱落了,可是还留有一个副本。郭象这个人,为人品行不好,却是才智出众。他看到向秀所释新义在当时没有流传开,便偷来当做自己的注。于是自己注释了《秋水》《至乐》两篇,又改换了《马蹄》一篇的注,其余各篇的注,有的只是改正一下文句罢了。后来向秀释义的副本发现了,所以现在有向秀、郭象两本《庄子注》,其中的内容是一样的。
阮宣子很有名望,太尉王夷甫见到他时间道:“老子、庄子和儒家有什么异同?”阮宣子回答说:“将无同。”太尉很赞赏他的回答,调他来做下属。世人称他为“三语椽”。卫玠嘲讽他说:“只说一个字就可以调用,何必要借助三个字!”宣子说:”如果是天下所仰望的人,也可以不说话就能调用,又何必要惜助一个字呢!”于是两人就结为朋友。
散骑郎裴逻娶太尉王夷甫的女儿为妻。婚后三天,王家邀请诸女婿聚会,当时的名士和王、裴两家子弟齐集王家。郭子玄也在座,他领头和裴遐谈玄。子玄才识很渊博,刚交锋几个回合,还觉得不痛快。郭子玄把玄理铺陈得很充分;裴遐却慢条斯理地梳理前面的议论、义理情趣都很精微,满座的大部赞叹不已,表示痛快。王夷甫也以为新奇罕见,于是对大家说:“你们不要再辩论了,不然就要被我女婿困住了。”
卫玠避乱渡江之初,去拜见大将军王敦。由于夜坐清谈,大将军便邀来谢幼舆。卫玠见到谢幼舆,非常喜欢他,再也不理会王敦,两人便一直清谈到第二天早晨,王敦整夜也插不上嘴。卫玠向来体质虚弱,常常被他母亲管束住,不让他多谈论;这一夜突然感到疲乏,从此病情加重,终于去世。 过去有种说法,说丞相王导到江南以后,也只是谈论声无哀乐、养生和言尽意这三方面的道理而已,可是这已间接关系到人的一生,是能渗透到每一个方面的。
中军将军殷浩任庾亮属下的长史时,有一次进京,丞相王导为他把大家聚在一起,桓温、左长史王濛、蓝田侯王述、镇西将军谢尚都在座。丞相离座亲自去解下挂在帐带上的拂尘,对殷浩说:“我今天要和您一起谈论、辨析玄理。”两人一起清谈完后,已到三更时分。丞相和殷浩来回辩难,其他贤达丝毫也没有牵涉进去。彼此尽情辩论以后,丞相便叹道:“一向谈沦玄理,竟然还不知道玄理的本源在什么地方。至于旨趣和比喻不能互相违背,正始年间的清谈,正是这样的呀!”第二天早上,桓温告诉别人说:“昨夜听殷、王两人清谈,非常美妙。仁祖也不感到寂寞,我也时时心有所得;回头看那两位王属官,就活像身上插着漂亮羽毛扇的母狗一样。”
中军将军殷浩看了佛经,说:“玄理也应当在这里面。”
谢安年轻时候,请光禄大夫阮裕讲解《白马论》,阮裕写了一篇论说文给谢安看。当时谢安不能马上理解阮裕的话,就反复请教以求全都理解。阮裕于是赞叹道:“不但能够解释明白的人难得,就是寻求透彻了解的入也难得!”
诸季野对孙安国说:“北方人做学问,深厚广博而且融会贯通。”孙安国回答说:“南方人做学问,清新通达而且简明扼要。”支道林听到后,说;“对圣贤,自然不用说了,从中等才质以下的人来说,北方人读书,像是在敞亮处看月亮;南方人做学问,像是从窗户里看太阳。”
刘真长和殷渊源谈玄,刘真长似乎有点理亏,殷渊源便说:“怎么你下想造一架好云梯来仰攻呢?”
中军将军殷浩说:“康伯还没有学到我牙缝里的一点聪明。”
镇西将军谢尚年轻时,听说殷浩擅长清谈,特意去拜访他。殷浩没有做过多的阐发,只是给谢尚提示好些道理,说了几百句话;不但谈吐举止有风致,加以辞藻丰富多采,很能动人心弦,使入震惊。谢尚全神贯注,倾心向往,不觉汗流满面。殷浩从容地吩咐手下人:“拿手巾来给谢郎擦擦脸。” 桓温聚集许多著名人士讲解《周易》,每天解释一卦。简文帝本想去听,一听说是这样讲就回来了,说:“卦的内容自然是有难有易,怎么能限定每天讲一卦呢!”
有位从北方过江来的和尚很有才思,他们支道林和尚在瓦官寺相遇,两人一起研讨《小品》。当时竺法深和尚、孙兴公等人都去听。这位和尚的谈论,屡次都设下疑难问题,支道林的答辩分析透彻,言辞气概都很爽朗。这位和尚总是被驳倒。孙兴公就问竺法深说:“上人应该是顶风上的人士,刚才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?”竺法深笑笑,没有回答。支道林接口说:“白檀香并不是不香,但逆风怎能闻到香呢!”竺法深体会到这话的含义,坦然自若。置之不理。
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,两人来回辩驳,精心竭力,宾主都无懈可击。侍候的人端上饭菜也顾不得吃,饭菜凉了又热,热了又凉,这样已经好几遍了。双方奋力甩动着拂尘,以致拂尘的毛全部脱落,饭菜上都落满了。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。殷浩便对孙安国说:“你不要做硬嘴马,我就要穿你鼻子了!”孙安国接口说:“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,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!”
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一篇,历来是个难点,名流们全部可以钻研、玩味,可是对它的义理的阐述却不能超出郭象和向秀。有一次,支道林在白马寺里,和太常冯怀一起谈论,便谈到《逍遥游》。支道林在郭、向两家的见解之外,卓越地揭示出新颖的义理,在众名流之外提出了特异的见解,这都是诸名流探求、玩味中没能得到的。后来解释《逍遥游》便采用支道林阐明的义理。
中军将军殷浩曾到丹阳尹刘惔那里去清谈,谈了很久,殷浩有点理亏,就不住地用些浮辞来应对,刘淡也不再答辩。殷浩走了以后,刘惔就说:“乡巴佬,硬要学别人发这样的议论!”
中军将军殷浩虽然才思精深广阔,可是独对才性问题最为精到。他随便地谈到《四本论》,便像汤他铁城,使人找不到可以进攻的机会。
支道林和尚写了《即色论》,写好了,拿给北中郎将王坦之看。王坦之一句话也没说。支道林说:“你是默记在心吧?”王坦之说:“既然没有文殊菩萨在这里、谁能赏识我的用意呢!”
王逸少出任会稽内史,初到任,支道林也在郡里。孙兴公对王逸少说:“支道林的见解新颖,对问题有独到的体会,心里所考虑的实在美妙,你想见见他吗?”王逸少本来就有超人的气质,很轻视支道林,后来孙兴公和支道林一起坐车到王逸少那里,王总是着意矜持,不和他交谈。不一会儿支道林就告退了。后来有一次正碰上王逸少要外出,车子已经在门外等着,支道林对王逸少说:“您还不能走,我想和您稍微谈论一下。”于是就谈论到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支道林一谈起来,洋洋数千言,才气不凡,辞藻新奇,像繁花灿烂,交映生辉。王逸少终于脱下外衣不再出门,并且留恋不止。
三乘的教义是佛教中很难讲解的,支道林登座宣讲,详加辨析,使三乘内容显豁。大家在下座听讲,都说能够理解。支道林离开讲坛后,大家自己互相说解,又只能解通两乘,进入三乘便混乱了。现在的三乘教义,弟子们虽然传习,仍然不能全部理解。
司徒掾许询年轻时,人们拿他和王苟子并列,许询非常下服气。当时许多名上和支道林法师一起在会稽的西寺讲沦,王苟子也在那里。许询心里很不平,便到西寺去和王苟子辩论玄理,要一决胜负。许询极力要挫败对方,结果王苟子被彻底驳倒。接着许询又反过来用王苟子的义理,王苟子用许询的义理,再度互相反复陈说,王苟子又被驳倒。许询就问支法师说:“弟子刚才的谈论怎么样?”支道林从容地回答说:“你的谈论好是好,但是何至于要互相困辱呢?这哪里是探求真理的谈法啊!”
支道林和尚去拜访谢安。当时东阳太守谢朗还年幼,病刚好,身体还禁不起劳累,和支道林一起研讨、辩论玄理,终于弄到互相困辱的地步。他母亲王夫人在隔壁房中听见这样,就一再派人叫他进去,可是太傅谢安把他留住。王夫人便只好亲自出来,说:“我早年寡居,一辈子的寄托,只在这孩子身上。”于是流着泪把儿子抱回去了。谢安告诉同座的人说:“家嫂言辞情意部很激愤,很值得传诵,可惜没能让朝官听见!”
支道林和司徒椽许询等人一同在会稽王的书房里讲解佛经,支道林为主讲法师,许询做都讲。支道林每阐明一个义理,满座的人没有不满意的;许询每提出一个疑难,大家也无不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大家只是一齐赞扬两家辞采的精妙,并不去辨别两家义理表现在什么地方。
车骑将军谢玄还在服父丧期间,支道林和尚就去他家和他谈玄,太阳快下山了才告辞出来。有人在路上碰见支道林,问道:“林公从哪里来呀?”支道林回答说:“今天和谢孝畅谈了一番呢。”
支道林刚从会稽来到建康时,住在东安寺里。左长史王濛事先想好精微的义理,并且想好富有才情、文采的言辞,去和支道林清谈,可是和支道林的谈论不大相称。王濛作长篇论述,自以为讲的是至理名言,用的是奇丽辞藻。支道林听后,慢吞吞地对他说:“我和您分别多年,看来你在义理、言辞两方面全都没有长进。”王濛非常惭愧地告辞走了。
中军将军殷浩读佛经《小品》,很多地方有疑难,加了二百张字条标明,这些都是精深奥妙的地方,是当时隐晦难明的。殷浩曾经想和支道林辩明这些问题,终究不能如愿。现在《小品》还保存下来。
佛经认为摆脱烦恼、修练智慧,就可以成佛。简文帝说:“不知是否就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?然而,道家陶冶锻炼的功效,还是不可以抹杀的。” 于法开和尚起初和支道林争名,后来大家的心意逐渐倾向于支道林,他心里非常不服气,便到剡县隐居起来。有一次,于怯开派弟子到京都去,吩咐弟子经过会稽山阴县,那时支道林正在那里宣讲佛经例、品》。于法开提醒他的弟子说:“道林开讲《小品》,等你到达时,就该讲某品了”于是给弟子示范,告诉他来回数十次的攻洁辩难,并且说:”过去这里面的问题不可能比我讲的更明白了。”弟子照他的嘱咐去拜访支道林。正好碰上支道林宣讲,便小心地陈述于法开的见解,两人来回辨论了很久,支道林终于辩输了。于是厉声说:“您何苦又给人托运呢!”
中军将军殷浩问道:“大自然赋予人类什么样的天性,本来是无心的,为什么世上恰恰好人少,坏人多?”在座的人没有谁回答得了。只有丹阳尹刘淡回答说:“这好比把水倾泻地上,水只是四处流淌、绝没有恰好流成方形或圆形的。”当时大家非常赞赏,认为是名言通论。
康僧渊刚到江南的时候,还没有人了解他、经常在街市商场上徘徊,靠乞讨来养活自己。一次,他突然到殷渊源家去,正碰上有很多宾客在座,殷渊源让他坐下,和他稍为寒暄了几句,便谈及义理。康僧渊的言谈意趣,竟然毫无愧色;不管是有深刻领会的,还是粗略提出的义理,都是他一向深入钻研过的。正是由于这次清谈,大家才了解了他。
殷浩、谢安等人聚会在一起。谢安便问殷浩:“人们用眼睛去看一切物象,一切物象是否就会进入眼睛呢?”
有人间中军将军殷浩:“为什么将要得到官爵就梦见棺材,将要得到钱财就梦见粪便?”殷浩回答说:“官爵本来就是腐臭的东西,因此将要得到它时就梦见棺材尸体;钱财本来就是粪土,因此将要得到它时就梦见肮脏的东西。”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名言通论。
中军将军殷浩被免职,迁到东阳郡,这才看佛经。开始看《维摩诘经》,怀疑“般若波罗密”这句话大多了;后来看《小品》,已经了解了这句话的意旨,又可惜这样的话太少了。
支道林、殷渊源都在相王府中,相王对两人说道:“你们可以试着辩论一下。可是才性关系问题恐怕是渊源的坚固堡垒,您可要谨慎啊!”支道林开始论述问题时,便改变方向,远远辟开才性问题;可是论辩了几个回合,便不觉进入了渊源的玄理之中。相王拍着肩膀笑道:“这本来是他的特长,你怎么可以和他争胜呢!”
谢安趁子侄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,问道:“《诗经》里面哪一句最好?”谢玄称赞说:“最好的是‘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’”谢安说:“应该是“訏谟定命,远猷辰告’最好。”他认为这一句特别有高雅之土的深远意趣。
张凭察举为孝廉后,到京都去,他仗着自己有才气,认为必定能厕身名流。想去拜访丹阳尹刘真长,他的同乡和一同察举的入都笑话他。张凭终于去拜访刘真长,这时刘真长正在洗谬和处理一些事务,就把他安排到下座,只是和他寒暄一下,神态心意都没有注意他。张凭想自己开个头谈谈,又找下到个话题。不久,长史王濛等名流来清谈,主客间有不能沟通的地方,张凭便远远地在未座上给他们分析评判,言辞精炼而内容深刻,能够把彼此心意表述明白,满座的人都很惊奇。刘真长就请他坐到上座,和他清谈了一整天。于是留他住了一夜。第二天,张凭告辞对,刘真长说:“你暂时回去,我将邀你一起去谒见抚军。”张凭回到船上,同伴问他在哪里过夜,张凭笑笑,没有回答。不一会儿,刘真长派郡吏来找张争廉坐的船,同伴们很惊愕。刘真长当即和他一起坐车去谒见抚军。到了大问口,刘真长先进去对抚军说:”下官今天给您找到一个大常博士的最佳人选。”张凭进见后,抚军和他谈话,不住赞叹,连声说好,并说:“张凭才华横溢,是义理篓革之所。”于是就任用他做太常博士。
汰法师说:“六通和三明同一指归,只是名称不同罢了。”
支道林、许询、谢安诸位品德高尚人士,一起到王濛家聚会。谢安环顾左右对大家说:“今天可以说是贤士雅会。时光既不可挽留,这样的聚会当然也难常有,我们应该一起谈论吟咏,来抒发我们的情怀。”许询便问主人有没有《庄子》这部书,主人只找到《渔父》一篇。谢安看了题目,便叫大家一个个讲解其义理。支道林先讲解,说了七百来句后,说解义理精妙优美,才情辞藻新奇拔俗,大家全都赞好。于是在座的人各自谈完了自己的体会。这时谢安问道:“你们说完了没有?”都说:“今天的谈论,很少有保留,没有不尽意的了。”谢安然后大致提出,一些疑问,便畅谈自己的意见,洋洋万余言,才思敏锐高妙,特异超俗,这已经是难以企及了,加上情意有所比拟、寄托,潇洒自如,满座的人无下心悦诚服。支道林对谢安说:“您一向抓紧钻研,自然很优异呀!”
中军将军殷浩、孙安国、王濛、谢尚等擅长清谈的名士,全在会稽王官邸聚会。殷浩和孙安国两人一起辩论《易象妙于见形论》一文,孙安国把它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谈论时,显得意气高昂。满座的人都觉得孙安国的道理不妥,可是又不能驳倒他。会稽王很有感慨地叹息道:“如果刘真长来了,自然会有办法制服他。”随即派人去接刘真长,这时孙安国料到自己会辩不过。刘真长来后,先叫孙安国谈谈自己原先的道理。孙安国大致复述一下自己的言论,也觉得很不如刚才所讲的。刘真长便发表了二百来句话,论述和质疑都很简明、贴切,孙安国的道理便被驳倒了。满座的入同时拍手欢笑,赞美不已。
僧意住在瓦官寺,王苟子到来,和他一起谈玄理,便让他先开个头。僧意问王苟子:“佛有感情没有?”王说:“没有”。僧意又问道:“那么佛像柱子一样吗?”王说:“像筹码,虽然没有感情,可是使用它的入有感情。”僧意又问:“谁来使用佛呢?”王苟子回答不了就走了。
太傅司马道于问车骑将军谢玄:“惠子所著的书有五车之多,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涉及玄言?”谢玄回答说:“这当然是因为玄言的精微处难以言传。” 中军将军殷浩被罢官后,迁居东阳,大读佛经,都能精通其义理,只有读到事数处理解不了、便用字条标上。后来碰见一个和尚,就把标出的问题拿来请教,便都解决了。
殷仲堪深入地考究了道家的学说,人们认为他没有哪方面不研究的。殷仲堪却叹息说:“如果我能解说《四本论》,言谈就不只是现在这样了!” 荆州刺史殷仲堪问惠远和尚:“《周易》用什么做本体?”惠远回答说:“《周易》用感应做本体。”殷又问:“西边的铜山崩塌了,东边的灵钟就有感应,这就是《周易》吗?”惠远笑着没有回答。
羊孚的弟弟羊辅娶王永言的女儿为妻。当王家要接待女婿的时候,羊孚亲自送他弟弟到王家。这时王永言的父亲王临之还活着,殷仲堪是王临之的女婿,也在座。羊孚很擅长名理,便和殷仲堪谈论《庄子·齐物论》。殷仲堪反驳了羊孚的见解,羊孚说:“您经过四个回合后将要见到彼此的见解相同。”殷仲堪笑着说:“只能说尽,为什么一定会相同!”等到四个回合后两人见解竟然相通了。殷仲堪感慨他说:“这样,我就没有什么见解跟你不同了!”并且久久地赞叹羊孚是后起之秀。
殷仲堪说:“三天下读《道德经),就会觉得舌根发硬。”
提婆刚到京都不久,就被请到东亭侯工地家讲解《阿毗昙经)。刚第一次开讲,僧弥坐到中途就说:“我已经全都懂了。”随即在座中分出几个有见解的和尚,另外到别的房间里自己讲解。提婆讲完后,王珣法冈和尚道:“弟子还一点也没有理解,阿弥哪能已经理解了呢?他的心得怎么样?”法冈说:“大体上都领会得对,只是稍为不够精密翔实就是了。”
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在一起谈玄,每每互相辩驳,一年多以后,辩驳少了,只有一两次。桓玄自己慨叹才思越来越倒退了,殷仲堪说:“这其实是您便加领悟了。”
魏文帝曹丕曾经命令东阿王曹植在七步之内作成一首诗,作不出的话,就要动用死刑。曹植应声便作成一诗:“煮豆持作羹,漉菽以为汁。箕在釜下燃,豆在釜中泣;本自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!”魏文帝听了深感惭愧。
魏朝封晋文王司马昭为晋公,准备好了加九锡的礼物,司马昭坚决推辞,不肯受命。朝中文武官员将要前往司马昭府第恭请接受,这时司空郑冲赶紧派人到阮籍那里求写劝进文。阮籍当时在袁孝尼家,隔宿酒醉未醒,被人扶起来,在木札上打草稿,写完,无所改动,就抄好交给了来人。当时人们称他为神笔。
左恩写《三都赋),刚写完,当时的人交相讥笑非难,左思心里很不舒服。后来他把文章拿给张华看,张华说:“这可以和《两都》《二京》鼎足而三。可是您的文章还没有受到世人重视,应当拿去通过名士推荐。”左思便拿去请教并恳求皇甫谧。皇甫谧看了这篇赋,很赞赏,就给赋写了一篇叙文。干旱先前非难、怀疑这篇赋的人,又都怀着敬意赞扬它了。
刘伶写了一篇(酒德颂》,这是他自己心意情趣的寄托。
尚书令乐广擅长清谈,可是不擅长写文章。他想辞去河南尹职务,便请潘岳替他写奏章。潘岳说:“我可以写呀,不过必须知道您的意图。”乐广便给他说明自己决定让位的原因,说了二百来句话。潘岳把他的话径直拿来重新编排一番,便成了一篇名作。当时的人都说:“如果乐广不借重潘岳的文辞,潘岳不甲乐广的意思,就无法写成这样优美的文章了。”
夏侯湛写成了《周诗》,拿去给潘安仁看,潘安仁说:“这些诗不但写得温煦高雅,另外也能见出孝顺友爱的情性。”潘安仁也因此写了《家风诗》。 孙子荆为妻子服丧期满后,作了一首悼亡诗,拿给王武子看。王武子看后说:“真不知是文由情生,还是情由文生!看了你的诗感到悲伤,也增加了我对夫妻精义的珍重。”
大叔广很有口才,挚仲治却擅长写作,两人都但任卿的官职。每当官府聚会,太叔广谈论,仲治不能对答;仲治回去写成文章来反驳,太叔广也不能对答。
东晋时、太常殷融和侄儿殷浩都擅长谈玄理,但是两人也有能言善辩和不善于言谈之别。扬州刺史殷浩的口头辩论是最厉害的,殷融辩不过他的时候总说:“你再想想我的道理。”
庾子嵩写成了《意赋》。他的侄儿庾亮看见了,问道:“如果有那样的心意呢。那不是赋体能说尽的;如果没有那样的心意呢,又写赋做什么?”庾子嵩回答说:“正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。”
郭景纯有两句诗:“林无静树,川无停流。”阮孚评价说:“川流汹汹,山风呼啸,的确不可言传。每当读到这两句,总觉得心身都超尘脱俗了。” 庾阐当初写《扬都赋》,赋中称赞温峤和庾亮说:“温氏树立起道义的准则,庾氏成了人们仰慕的对象。比拟其声音,那就像铜钟的音响那样铿锵;比拟其品德,那就像宝玉一样晶莹发亮。”庾亮听说赋已经写好了,就要求看看,同时希望送给自己。于是庾阐又把其中的“望”字改为“俊”字,把“亮”字改为“润”字等等。
孙兴公写了《庾公诔》,袁羊看了以后说:“从文章中能看出这种一张一弛的治国之道。”在当时,人们认为这是著名的鉴赏评语。
庾仲初写完了《扬都赋),把它呈迭给庾亮,庾亮出于同宗的情分,大力抬高这篇赋的声价,说它可以和《两都赋》《二京赋》《三都赋》等名篇比美。从此人人争着传抄,京都建康的纸张也因此涨价了。太傅谢安说:“不能这样写,这是屋上架屋呀,如果写文章处处都模仿别人,就免不了内容贫乏,视野狭窄了。”
习凿齿冶史的才学很下寻常,桓温非常看重他,还没到三十岁,就任用他为荆州治中。凿齿在给桓温的答谢信里也说:“如果不是受到阁下的赏识,我只是荆州的一个老从事罢了!”后来桓温派他到京都去见丞相,回来报告的时候,桓温问:“你见了相王,觉得他怎么样?”凿齿回答说:“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的人”由此触犯了桓温。被降职出任衡阳郡太守,从此神志就错乱了。他在病中还坚持写《汉晋春秋》,品评人物、史实,见解卓越。
孙兴公说:“《三都赋)和《二京赋》是五经的翅膀。”
太傅谢安问主簿陆退:“张凭为什么作悼念母亲的诔文,而不作悼念父亲的?”陆返回答说:“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;而妇女的美德,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。”
王敬仁十三岁写了《贤人论》一文,他父亲王濛送去给刘真长看,刘真长看后答复说:“看了敬仁所写的论文,就知道他能够参悟玄言了。”
孙兴公说:“潘岳的文章好像摊开锦绣一样文采斑斓,没有一处不好;陆机的文章好像披沙拣金,常常能发现瑰宝。”
简文帝称赞司徒掾许玄度说:“玄度的五言诗。可以说精妙过人。”
孙兴公写成了《天台赋》,拿去给范荣期看,并且说:“你试把它扔到地上,定会发出金石般的声音。”范荣期说:“恐怕您的金石声,是不成曲调的金石声。”可是每当看到优美的句子,总是说:“这正该是我们这些人的语言。”
桓温看见谢安石所作的给简文帝谥号的奏议,看完了,扔给座上的宾客说:“这是安石的零碎金子。”
袁虎年轻时家里很穷,曾经受雇替人运送租粮。这时,镇西将军谢尚坐船出游,那一夜风清月明,忽然听见江边商船上有人吟诗,很有情味;所吟诵的五言诗,又是自己过去未曾听过的,不禁赞叹不绝。随即派人去打听底细,原来是袁虎吟咏自作的《咏史诗》。因此便邀请袁虎过来,对他非常赞赏,彼此十分投合。
孙兴公说:“潘岳的文章浅显,可是纯净,陆机的文章深刻,可是芜杂。” 裴启写了《语林》一书。刚拿出来,远近的人广为传看。当时名流和后生年少,没有谁不传抄,人人手执一卷。其中记载东亭侯王珣作《经王公酒沪下赋)一事,很有才情。
谢万写了《八贤论》,并就其内容和孙兴公来回辩论,稍有胜负。谢万后来把文章拿出来给顾君齐看,顾君齐说:“如果我也写这几个人,料你一定会标不出题目来。”
桓温叫袁彦伯作一篇《北征赋》,赋写好以后,桓温和在座的贤士一起阅读,大家都赞叹写得好。当时王珣也在座,说:“遗憾的是少了一句。如果用“写”字足韵,就会更好。”袁彦伯立刻即席拿笔增加了一句:“感不绝于余心,溯流风而独写。”桓温对王珣说:“从这件事看,当今不能不推重袁氏。”
孙兴公谈论到曹辅佐时说:“他的文才就像一幅白底子的明光锦,裁成了差役穿的裤子,这不是没有文采,只是太没个剪裁了。”
袁彦伯写成了(名士传),带去见谢安,谢安笑着说:“我曾经和大家讲过江北时期的事,那不过是说着好玩罢了,彦伯竟拿来写书!”
东亭侯王珣到任所就任桓温的属官,已经到了官署里,桓温叫人偷偷拿走了他的报告。王珣立即在官署里重新写,没有一个字和前一报告重复。
桓温率师北伐、当时袁虎也随从出征,因事受到桓温的责备,罢了官。正好急需写一份告捷公文,桓温便叫袁虎起草。袁虎靠在马旁,手不停挥,一会儿就写了七张纸,写得很好。当时东亭侯王地在旁边,极力赞赏他的才华。袁虎说:“也该让我从齿舌中得点好处。”
袁宏起初写《东征赋》的时候,没有一句话说到陶侃。陶侃的儿子胡奴就把他骗到一个密室里,拔出刀来指着他,问道:“先父的劝勋业绩这样大、您写《东征赋》,为什么忽略了他?”袁宏很窘急,无计可施,便回答说:“我大大地称道陶公一番,怎么说没有写呢?”于是就朗诵道:“精金百炼,在割能断。功则治人、职思靖乱。长沙之勋,为史所赞。”
有人问顾长康:“您的《筝赋》和嵇康的《琴赋》相比,哪一篇更好?”顾长康回答说:“不会鉴赏的人认为我的后出就遗弃它,鉴赏力强的人也会因为高妙新奇而推许我。”
殷仲文天赋甚高,可是读书不甚广博。傅亮感叹说:“如果殷仲文读的书能有袁豹的一半,才华就不次于班固。”
羊孚写了一篇《雪赞》,其中说:“资清以比,乘气以霏。遇象能鲜,即洁成辉。”桓胤便把这两句写在扇子上。
王孝伯在京的时候,一次行散到他弟弟王睹门前,问王睹古诗里头哪一句最好。王睹工考虑,还没有回答。孝伯吟“所遇无故物,焉得不速老!”说:“这句是最好的。”
桓玄有一次登上江陵城城墙的南楼,说道:“我现在想给王孝伯写一篇诛文。”于是长时间吟咏歌啸,接着就动笔。只坐一会儿的功夫,诔文便写成了。
桓玄刚同时管辖西部一带,兼任荆、江两州刺史,任两个府的长官,还袭封了一个侯国。这年初次下雪,五处官府都来祝贺,五封贺信一起送到。桓玄在官厅上,贺信一到,就在信后起草复信,每封信都下笔成章,文采斑斓,而且不相混同。
桓玄东下京都,当时羊孚任充州别驾,从京都来登门拜访,他给桓玄的求见信上说:“自从不久前因为战乱分别,我也意志消沉,心情郁结,明公给漫漫长夜迭来晨光,用一源澄清百流。”桓玄见到信,赶紧把他请上前来,对他说:“子道,子道,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!”立即任他做记室参军。当时孟昶在刘牢之手下任主簿,来登门向羊孚告辞,见面就说:“羊侯,羊侯,我一家百口就托付你了。”
栏目最新
- 1 《风月鉴·第04回 辞艳 寻芳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2 《风月鉴·第03回 戏墨 误宴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3 《风月鉴·第02回 幻梦 刁宴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4 《风月鉴·第01回 投胎 解笑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5 《商君书·弱民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6 《商君书·立本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7 《商君书·更法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8 《商君书·战法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9 《商君书·错法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10 《商君书·壹言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11 《商君书·开塞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12 《商君书·算地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13 《商君书·说民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14 《商君书·去强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
- 15 《商君书·农战》在线阅读,翻译及赏析